经常会碰到餐饮界里的老板或厨师长🔥,诉说开餐饮的不易➜,尤其是所谓菜品的出新创新🚆,很是头疼。不出吧,客人吃吃就不愿光顾了🧒🏽,出吧🚴🏿,很难把握需求点和创新点。这的确是个问题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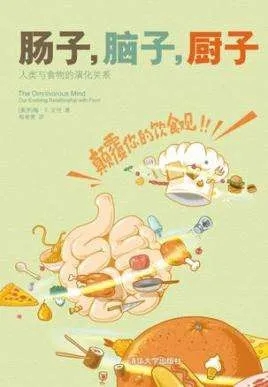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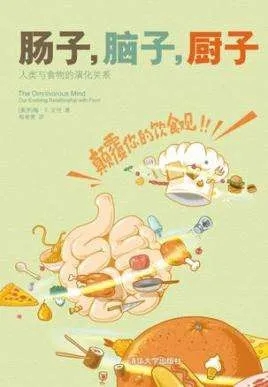
近读美国学者约翰.艾伦写的《肠子,脑子,厨子》一书,颇有启发。他在“咀嚼与脑”一章中对人类进食的咀嚼与产生愉悦的大脑的关系,进行了科学探讨和仪器验证,得出的结论,颇为有趣⏸。他说🧥,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,在于人类有了意识,体现在人的语言和学习推理创造功能上🙇🏻♂️,动物是不具备的📸。同样👩🏽⚕️,人类的进食和动物的进食也绝不一样。动物的进食💆♀️,是纯生存需求行为,饿了就吃,能吃到什么就吃什么,吃饱就得👩🏻🦱🤜🏼。而人的进食👻⚓️,尤其是咀嚼吞咽🥲,除了也受到生存需求控制外(饿了就想吃)👮🏼♂️👼🏽,还受到意识的支配。他进而通过对大脑的详细解剖分析(此处省略1000字),得出的结论是👂🏻,人的大脑皮层,分为两个区域🏊🏽,一个叫做初级皮质,另一个叫做联合皮质;前者负责听觉视觉运动控制等感官输入,这个动物的大脑也有。后者(联合皮质)是人类大脑经过进化所独有的,负责人类的高级认知🧛🏿,如思考、决策🐈、创造等。而联合皮质(大脑的高级区)对人类的进食也起决定作用👍🏽。比如🌻⛈,人在饥饿时👩🏻🦯,进食红烧猪肉,咀嚼的愉快感应该是强烈的,因为“喜爱熟肉食是人类区别于猿人的主要特征之一”,但如果是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信徒,一块瘦肉咀嚼一半时,你告诉他这是猪肉,他会立即停止进食,并有可能引发呕吐👩🏼⚕️。这时🎠,宗教的意识出来干涉了咀嚼,说明,人类的咀嚼进食是受到意识的支配的👩🏿🎤,而动物却不会有类似的反应⛔️。

进而,他又举例和试验,在人们咀嚼食物时🙇♂️,给咀嚼者输入不同信息🧑🏿,测量出的脑血流量和脑波是不同的。比如🚴🏽♀️,人咀嚼一道食物,给不同的语言信息🫃,脑血流量和脑波是不一样的,假如一道菜,你告知他这是耶稣最爱吃的圣餐,或是某地某国顶级美食,他甚至会激动产生“嚼吞高潮”(foodgasm)发出兴奋的怪叫👩🏽🌾。而动物却没有反应🫗🙅🏻,脑血流量和脑波不会有任何反应🗳,因为动物不懂语言,听不懂故事,只能是对牛弹琴。充分说明一点🕜,人对食物除了满足咀嚼的享受外,更有意识来支配🫵🏼🥩,人和动物对待食物的最大的区别,就在于选择的意识性🛏,美食是有境界的!换句话说,有故事的🔦,有文化的饮食,处于大脑选择的前段。比如,两年前桌前有几盘不同的包子🉑🫘,如果就是为了裹腹🍂,通常你可能选择肉包子🅾️;但有人告诉你👷🏽♀️,其中哪盘是乾隆帝爱吃的蟹黄包子,你可能就会选择扬州蟹黄包子来品尝🙇♀️。
这个老外的理论实验和结论🪺,正好和我们中华饮食理论强调美食的独特性、厨艺性🏇🏻、故事性🍕、文化性不谋而合🍸🐲!所以🏀,挖掘和开发饮食的上述四性👨🏻🚀,让人们吃美食不仅仅是只满足裹腹吃饱,就是我们饮食文化人的责任、方向和境界🏋🏻。
意识决定选择🫱🏿🔞!意识决定选择!意识决定选择🧦!—重要的话说三遍!



